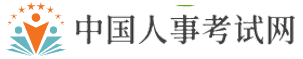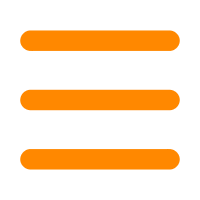生成式AI对常识产权法律规范的冲击,尤其是对著作权法的拷问,已成为当下无法避免的热门问题。然而,《生成式AI服务管理暂行方法》已经确立了生成式AI服务提供者的法律主体地位,从而不承认了生成式AI法律主体说的可行性。而京0491民初11279号判决书作为人工智能生成图片著作权侵权第一案,又一定了生成式AI生成的内容作为作品,并可以遭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这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生成式AI所带来的冲击,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生成式AI会不会引起著作权法上合理用规范的变革。
1、生成式AI与著作权法的碰撞
生成式AI的本质———著作权侵权的现实可能
以ChatGPT为例,它是一种基于Transformer互联网和无监督学习技巧的生成式对话模型,具备数据剖析丰富性、信息获得便捷性、人机交互灵活性与问题回复筛选性等突出特征。ChatGPT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传统的“剖析式人工智能”不同,生成式AI愈加灵活和自动化,不只能理解和讲解数据的意思,还能依据输入的数据和资料,进行预测并输出全新文本,即生成式AI拥有不同于传统AI的独立决策能力。伴随技术的不断升级,将来的GPT版本或许会进一步扩大模型规模,以提升预测能力和处置复杂任务的能力,探索更高效的练习办法,同时减少对计算资源的占用和能源消耗,降低常识库的更新时间,并提升模型在实质应用中的可控性和安全性,还将持续关注模型的公平性和道德问题,进一步降低模型中存在的偏见和歧视[1]。
生成式AI的生命周期———著作权侵权的阶段风险
生成式AI的生命周期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模型练习阶段、模型运行阶段和模型再优化阶段。
1.模型练习阶段
服务提供者为生成式AI设计算法,优化运行,用数据“喂养”生成式AI来培养其生成能力。这样来看,这一阶段的数据合规性风险主要来自于服务提供者的数据练习行为,服务提供者或是用公共范围中的开放数据进行模型练习,或是向专业的数据采集方采购数据用以“喂养”模型。但无论哪一种方法,服务提供者所用的数据都可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作权侵权的风险。因此,这种数据练习行为在模型练习阶段依旧构成对著作权的侵犯,如不加以规制,之后模型运行阶段的侵害后果和影响范围会进一步扩大。
2.模型运行阶段
与生成式AI接触的主如果用户。用户通过对生成式AI输入指令或内容而后由生成式AI给出多样化的答案。在这一阶段,用户输入的指令或内容可能涉及第三方著作权,生成式AI用这类数据时,因未经著作权人授权,大概侵害著作权,且对于生成式AI的生成内容,假如用了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或作品片段,或者形成对作品的演绎,就会成为著作权法规制的对象。比如,ChatGPT问世后,有人就借助它生成了受著作权保护的书本的缩略版,用来帮助读者迅速阅念书籍,因为这种行为会干扰原书的市场流通,因此,非常可能被认定为侵害著作权的行为[2]。可见,模型运行阶段的著作权侵权非常可能是用户与服务提供者的一同侵权行为或竞合侵权行为。
3.模型再优化阶段
用户与服务提供者没办法直接接触到生成式AI,而是由生成式AI自己依赖算法和算力对模型练习阶段和模型运行阶段的数据进行反复学习以提高我们的生成能力。尽管服务提供者没办法直接干涉生成式AI的自主学习,但仍对生成式AI负有数据合规的义务。《暂行方法》第七条第二项规定,生成式AI优化练习阶段的数据处置活动涉及常识产权的,不能侵害别人依法享有些常识产权。因为生成式AI不拥有法律主体资格,因此,模型再优化阶段的著作权侵权本质上是前两个阶段服务提供者侵权行为的延伸。
2、生成式AI合理用的判例研讨
目前,海外已出现因生成式AI所引发的关于合理用标准认定的判例,初步对生成式AI与合理用规范的衔接进行了探索。
美国Goldsmith案的判决经历
2023年5月18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安迪·沃霍尔视觉艺术基金会诉戈德史密斯一案,判决已经过世艺术家安迪·沃霍尔依据已经过世歌手普林斯的照片创作的一系列丝网印刷作品侵有摄影师林恩·戈德史密斯的版权。起初,纽约南区地办法院并不觉得沃霍尔侵有戈德史密斯的版权,觉得沃霍尔满足美国《版权法》第107条所规定的合理用的要件,并于2019年作出有益于原告AWF的浅易判决。被告对此判决不服,上诉至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上诉法院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判决,觉得合理用的四个要点均有益于被告,即沃霍尔的该系列作品不构成合理用,侵有被告戈德史密斯的作品版权。原告AWF对该判决不服,随后将此案提交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集中审理了判断合理用的第一个要点,即“用的目的和性质,包含此类用是不是具备商业性质或用于非营利教育目的”。判决书中指出,“第一个合理用原因考虑的是对版权作品的用法是不是具备进一步的目的或不一样的性质,这是一个程度问题,而不一样的程度需要与用的商业性质相平衡”。并一定了“任何为原始材料添加新的美学或新的表达方法的二次创作都势必具备转换性”的看法,觉得法官不可以从艺术家的角度判断作品具备转换性,而应从客观视角衡量二创作品借助原创的目的与性质,与与原创作者的排他用权间的利益平衡。由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主要从用的目的和性质两方面剖析第一个要点有益于哪方:
本案中,1984年和2016年的出版物都刊有普林斯的肖像并介绍普林斯的故事,两次用照片或作品的环境不是“独特和不一样的”。因此,这两次用行为具备基本相同的目的。该行为使《橙色普林斯》构成对戈德史密斯原始照片的市场替代,这种相同的复制对原作品版权人而言是不公平的。AWF以10000USD的价格将《橙色普林斯》授权给康泰纳仕,将照片刊登在杂志上出版,该许可毫无疑问是商业性的。综合来看,目的和性质两个原因———戈德史密斯的照片和AWF2016年对《橙色普林斯》的许可实质上具备相同的目的,与AWF对戈德史密斯照片的用法具备商业性质———均不构成合理用。最后,2023年5月18日,索托马约尔法官在一份建议书中以7∶2的比率确认此案。
Goldsmith案引发对合理用的规范考虑
在Goldsmith案之前,美国的交互式计算机服务提供者将Campbel案所确立的合理用标准奉为圭臬。依据Campbel案,当受版权保护的作品传达“新的表达、意义或信息”时,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是变革性的。AWF在诉讼过程中也引用了这一判例,称其为“坎贝尔的意义或信息测试”,并断言该测试适用于所有对变革性用的剖析。因此,AWF觉得,尽管用与原文有相似之处,甚至是对原文的字面复制,但假如增加了新的意思,则具备变革性,并觉得它遵循了《版权法》的文本和目的。
但Goldsmith案改变了这一认定标准。该案了解地表明,尽管变革性是一个要紧的问题,但它不是第一个要点的唯一原因,且变革性不应仅以创作者的规范来判断,需结合一些客观性元素综合、全方位地断定,这就是AI公司应该关注这一决定是什么原因。生成式AI的工作原理是提取或处置很多人类生成的工作,然后练习模型依据输入的数据创建“新”的工作。其摄取的几乎所有数据,包含文本和图像人工智能,都未得到原始创建者的许可。这意味着AI是打造在很多受版权保护的材料之上的,而这类材料是在未经许可的状况下用的。在Campbel案所确立的合理用标准下,AI公司长期以来一直觉得,他们用这类原材料是被允许的,由于这是一种合理用。他们对此讨论的焦点主如果AI生成的作品具备什么样的变革性。然而,最高法院忽视了有益于AI企业的最好论据。目前,变革性需要与其他元素形成对比,最明显的问题是新作品怎么样在市场上与原作角逐或取代原作。
3、生成式AI合理用的规范重塑
“三步检验法”很难适应生成式AI的进步
合理用规范的渊源可追溯至英国普通法,其刚开始内涵是再创作的作者借助原创作品创作我们的作品可以获得版权。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在1986年判决指出,当第二个作者以创造和革新的方法用别人受保护的作品时,其结果是学术的进步而非剥削第一个作者[3]。由此观之,合理用规范的初衷是平衡著作权人与用户之间的利益关系,以调和作者权利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达成促进思想文化传播的目的。在规范定位上,合理用是受著作权限制的一种方法,通过限制权利行使方法、范围和界限,为著作权侵权提供抗辩。证成合理用的原因无外乎三类:不具备商业性目的;用占作品的数目较少;基于公共利益之考量。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合理用的判断性标准———“三步检验法”。这一标准也为国际社会所认同,在《伯尔尼公约》第9条第2款中有有关的规定:合理用限于某些特殊的状况下;不应与作品的正常借助相抵触;不能不合理地损害版权持有者的合法利益[4]。
依此标准,生成式AI恐很难达到。第一,数据对于生成式AI而言是基础性的养料,不可能仅在“特殊状况下”用数据,应为“常见且正常的”。
第二,《伯尔尼公约》的立法精神表明,“不应与作品的正常借助相抵触”实质含义是“所有具备或者可能具备重大经济或实质重要程度的作品借助方法,都应当保留给作者,对于这类作品借助方法,任何可能对作者的利益加以限制的例外都是不容许的”[5]。生成式AI对于作品最常见的方法即是复制,而这种抄袭行为正是著作权人最为反感的。可见,这明显与作品的正常借助“相抵触”。
最后,对于“不合理地损害”,应是指非基于公共利益需要对权利人的利益进行损害,这会对权利人的经济利益导致损失,而这种不合理损害可以通过经济方法予以补偿。一般,生成式AI生命周期中作品的利益并不是基于公共利益,假如需要生成式AI的服务提供者对著作权人予以经济补偿,则会给其带来巨大的经济重压,容易将这一新兴事物抹杀在摇篮中。可见,“三步检验法”与生成式AI的进步需要很难契合。
“转换性用”完美契合生成式AI需要
生成式AI合理用的规范,应当结合其技术原理及用目的有针对性地改革。具言之,可借鉴Goldsmith案的论证逻辑,着重对生成式AI服务提供者及用户对作品的用法目的是不是具备变革性进行考量,从而确定其是不是构成“转换性用”,并将此作为认定合理用的规范。
“转换性用”相较于“三步检验法”的优势主要有二。其一,“转换性用”更符合AI产业政策的需要。当下,各国均加强投入,加速AI的研发,以求占据新兴技术的进步高地,健全的法治要为生成式AI的进步云筑网。若以“三步检验法”为合理用之标准,则生成式AI服务提供者将面临高昂的数据本钱、侵权本钱甚至诉讼本钱,必然会迟缓其进步,与产业政策相悖,而“转换性用”则可以弥补这一缺点。
其二,“转换性用”能充分协调各方的利益诉求。生成式AI年代的到来,使得“重保护轻共享”的传统立法范式已很难适应现实之需,对著作权人的过度保护将阻滞文化的革新兴盛。因此,应当重新审视著作权法的价值,著作权法不只保护原创性内容,也应鼓励创作之后的用法行为,力争在著作权人的专有权利益与社会公众用和享受作品的利益之间达成平衡,而“转换性用”恰能符合这一价值需要。
结合生成式AI的技术原理及Goldsmith案的思路,“转换性用”应当把生成式AI服务提供者或用户的用法目的和性质作为认定的重点内容。除此之外,“转换性用”的认定应当依据“输入”和“输出”阶段而有所不同。输入阶段的转换性用,若是基于数据练习,则应认定为合理用之情形。由于人工智能的数据练习本身具备隐蔽性和非感知性,不是为了赏析作品中的“表达”,而是通过很多阅读概括出“素材”的结构性特点进而创建其我们的“规则”,与传统的作品用有实质性差异。所以,在一定量上,人工智能对作品的用法具备“私人用”“合理借鉴”“转换性用”的成分,从而具备传统著作权法上的正当性支持。而如果是基于私利之用,则应着重考察会不会“影响作品的正常用”或“侵犯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输出阶段的“转换性用”则应当采纳著作权法中的“实质相似”标准,人工智能作品与原作品构成“实质相似”,根据著作权法上“接触+实质相似”的侵权判断规则,从作品“输出”之时起不再是合理用的范畴,而应当是著作权人控制的范围[6]。由于人工智能作品会构成对原作品的市场替代,会对原作品版权人的利益导致“不合理”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