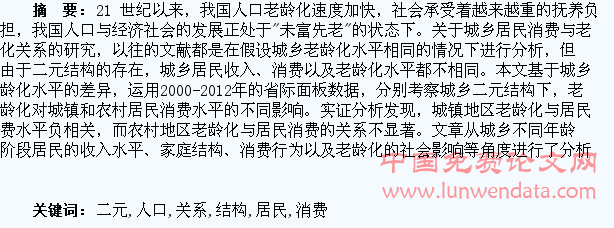
引言
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年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进步中国家都要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状况下探求自我进步的道路。自2000年起,国内65岁及以上人口数目达到了总人口数目的7%,年龄中位数超越35岁,正式步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导致了整个国家处于“未富先老”的情况下,即人口年龄的老化程度快于经济进步水平。一方面,医疗条件的改变、“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经济的转型与社会观念的改变使得国内人口年龄结构在短短的半个世纪历程了从相对年轻型的人口到老年型人口的转变。其次,虽然国内经济一直高速增加,但人均GDP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居民的人均收入及消费水平并不高,特别是近几年来国内的居民消费水平一直在低位徘徊,并且城乡消费差距也还十分明显。
如图1所示,2000年来,国内居民消费率逐年下滑,虽然这一趋势在2010年之后有所缓解,但居民消费率一直处在50%以下的水平,这与钱纳里等人提出的规范结构中工业化中期阶段65%的居民消费率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从图1中还可以看出国内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愈加大,到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为16674元,而农村居民仅为5908元。在影响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原因中,收入是一个主要原因。同时,城乡居民在消费观念、家庭年龄结构等方面也存在差距,特别是伴随城市化的进行,农村人口的很多迁移,使得落后的农村区域反而出现的更高的老龄化水平,并且国内城镇和农村的老龄化水平倒置状况还非常紧急,这对于居民的养老与城乡社会进步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那样,伴随国内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城乡老龄化水平的不同会不会对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产生影响呢?本文对此进行了研究。
文献综述
关于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最主要的理论依据就是莫迪利亚尼等人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依据这一假说,买家会将一生的预期总收入在不同年龄阶段进行最佳配置,以获得跨期功用最大化。
以该理论为基础,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多方探讨,力求得出老龄化与消费或储蓄之间的关系。Leff(1969)对1964年74个国家的截面数据作进行了经验剖析,结果表明人口抚养比和储蓄率存在负有关的关系。然而,随后的Goldberger(1973)与Ram(1982)则对leff的结论提出了质疑,他们通过实证研究觉得抚养比和储蓄率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Mopgliani and Cao(2004)使用国内1953-2000年时间序列数据,对人口老龄化与储蓄率的关系进行计量估计,研究结果觉得老龄化是国内出现高储蓄的一个主要原因。舒尔茨(2005)用16个亚洲国家和区域1952-1992年间的数据,借助动态面板回归的办法检验了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的影响,觉得老龄化会对储蓄率产生影响,但其影响是非常微弱的。国内学者方面,王金营、付秀彬(2006)对国内自1978年以来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剖析,引入标准消费人定义和变量,并证明了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水平、消费规模和消费结构均有肯定影响,并且老龄化水平的提升会减少将来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比率。李文星、徐长生、艾春荣(2008)借助动态面板GMM估计办法,对1989-200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估计,考察国内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发现少年抚养比与居民消费存在负有关的关系,但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于潇、孙猛(2012)通过对边际消费倾向的测算,觉得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路径主如果通过改变社会总体消费倾向来达成的,但在人口老龄化进步进程中的不同阶段,会对总消费需要产生不一样的影响。毛中根、孙武福、洪涛(2013)通过对1996-2010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测算,觉得老年抚养比的提升是致使居民消费减少的一个主要原因。并且人口老龄化的提升显著减少了城市居民的消费支出,而对农村居民的影响则不显著。
总之,国内外学者对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水平关系的研究到今天并无定论,而在进行城乡老龄化与消费水平关系剖析时,以住的文献也是假设同一省份或区域的城乡老龄化水平相同。但事实上,城乡老龄化水平并不相同,并且存在倒置现象。因此,本文分别对2000年至2012年的城镇和农村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剖析,重点考察城乡二元结构下,老龄化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并从城乡不同年龄阶段居民的收入水平、家庭结构、消费行为与老龄化对社会的影响等角度剖析上述结论。
城乡二元经济下老龄化与消费水平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数据了解明
为了研究在城乡二元结构下老龄化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本文使用了2000年到2012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打造面板数据模型。所有数据均源自《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因为西藏自治区人口较少,且抽样数据的波动性非常大,个别年份还存在数据缺失的状况,这严重干扰整体数据的稳定性,因此笔者剔除去该区域的数据。
在这里,模型的打造相对简单,只考虑消费与人口年龄结构和收入的关系,没考虑财政支出、利率、城市化及各地消费环境等原因的影响。该模型的重点在于研究老龄化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此选取的数据包含城乡的老年及少年抚养比与城乡居民的人均消费和支出。数据处置上,为了同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这两个变量相匹配,笔者将各区域城市及镇两个部分的老年及少年抚养比整理合并,得到城镇老年抚养比和城镇少年抚养比。该模型的居民收入与消费已扣除价格原因。 (二)计量模型设定
为体现城乡之间的差异,本文分别打造两个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基于面板数据的特征,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可以表述为:
(1)
(2)
这里,式(1)表示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方程,式(2)表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方程。其中,i表示经济地区,t表示时间,cons表示实质人均消费,old表示老年抚养比,young 表示少年抚养比,ln(income) 表示实质收入的对数值,对实质收入取对数的意义在于表示实质收入对实质消费支出的弹性,即衡量实质收入变化百分之一的状况下,实质消费量将会变化百分之几,从中也可以看出收入对城乡消费影响的差异。consit-1 和consit-2 表示滞后一期和两期的消费水平,用来衡量棘轮效应的大小,ε表示随机误差项。城镇和农村的方程架构和经济学意义相同。
对于面板数据模型参数的估计选择用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的二阶段GMM估计办法。在文献中,一般将他们二人提出的二阶段GMM估计办法称为标准一阶差分GMM估计。本文借助STATA12进行具体估计。
(三)实证结果
2000-2012年城镇与农村区域人口老龄化水平与居民消费关系的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老龄化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的影响并不相同,老龄化与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负有关,并通过了10%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同时,老年抚养比增加1个百分点,收入会降低21.49元。而老龄化与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的关系不显著。少年抚养比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存在正向的影响,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其中城镇少年抚养比增加1个百分点会促进城镇居民消费提升22.09元,农村少年抚养比增加1个百分点会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加15.11元。城乡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也非常显著,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每增加1%,平均消费水平会增加27.78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每增加1%,平均消费水平会增长10.49元。除此之外,城镇和农村居民都会遭到上一期和上两期消费水平的影响,其中上一期的影响更为显著,存在明显的棘轮效应。
城乡老龄化与居民消费关系实证结果剖析
第一,城镇居民的老年抚养比与消费水平负有关,重要原因在于:第一,城镇居民退休之后,收入降低,老大家需要动用之前的储蓄来养老,并且老年人自己也总是比较节俭,这会降低他们对自己的消费支出。第二,城镇区域生活相对富足的老大家有非常强的赠送动机。在国内,老大家的代际消费倾向较高,他们总是对我们的消费比较克制,但对后代则比较慷慨。特别是在子女购买住房、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上,老一辈的财富积累发挥了要紧有哪些用途。这也使得老年大家会自觉降低我们的消费,而主动将储蓄赠予后代。第三,国内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伴随“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少子化成为国内家庭现在面临的主要局面,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国内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1.18,其中城市为0.88,镇为1.15,农村为1.44,这与发达国家1.7的总和生育率相差不少。特别对于城镇区域的老年来讲,少子化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以后生活的不确定性增加。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孩子可以看作是居民为老年时老有所依所做的一种投资。但子女数目的降低使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大家不能不为预防将来生活的不确定性而增加储蓄,降低消费。其次,从剖析结果可以看出,老龄化与城镇居民消费的负有关关系仅通过了10%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这是因为一方面受传统的养老观念的影响,子女对爸爸妈妈的赡养会一部分地补偿老人退休之后的收入。其次,因为老年人来到生命的最后阶段,补偿消费心理比较强,一些年轻时没体验和享遭到的事物,他们期望可以在夕阳阶段得到补偿。因此,这也在一定量上促进了老年消费水平的提升。
第二,与城镇不同,农村居民的老年抚养比与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不显著,重要原因在于,农村区域居民收入来源与城镇不同,他们主要依赖我们的劳动收入。并且一些身体强健的老年还可以继续劳动。表2显示了2012年城镇和农村老年人主要收入来源。其中,农村区域有28.48%的老年人主要依赖我们的劳动获得收入。但,大多数老年人因为身体机能降低,不再劳动,收入降低,消费也会随之降低。但其次,如表2所示,农村区域超越半数的老年人还要依赖家庭成员的供养,这也会增加其他家庭成员的支出。且家庭成员对老年人不一样的赡养方法也会干扰家庭的消费水平。同时,因为农村家庭规模相对更大,子女相对较多,这对老人的赡养也更为有利。依据最新统计数据,2012年国内城市平均家庭规模为2.73人/户,这一指标,镇为3.09人/户,而农村则为3.19人/户。另外,因为农村区域的消费物资相对城市较为匮乏,特别在医疗保健、老年文化娱乐等方面,这不利于农村老年人消费水平的提升。总之,这类方面综合起来使得农村区域老龄化与居民消费的正负关系不明显。
第三,实证结果中还可以看出,城乡的少年抚养比与居民消费都呈正有关关系。这与之前多位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孩子的增加势必会带来家庭消费支出的增长。但,伴随家庭规模的缩小,孩子数目的降低,加上预防性动机的增强,这类都会降低居民消费水平。结论中还可以看出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呈显著正有关关系,但应该注意的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对人均消费影响的绝数值并不相同,城镇是农村的近三倍,并且从实证结果也可以看出,城乡收入的不同在非常大程度上影响了城乡消费水平的差异。另外,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还会遭到过去消费习惯的影响,棘轮效应比较明显。因此,消费水平的提升还需要一个过程。
另外,老龄化不只影响了老年人的消费水平,还会干扰其他家庭成员的消费,与全社会的消费预期。在国内,家庭养老仍然是最主要的养老方法,老年人口的增多,势必加强家庭养老支出。而现在,国内老龄化还表现为老龄人口数目大,老龄化速度快与高龄人口比重不断上升三大特征。预计到2020年,国内80岁以上高龄老人将达到2200万,这将是2012年的四倍以上。因为老年人身体机能与行为能力大大降低,需要特殊的照顾,这更会增加年轻子女的家庭负担。子女对老人的赡养在一定量上会提升老人的消费水平,但会干扰其他家庭成员的消费支出。同时,因为老龄化、高龄化已成为一种趋势,国内城乡居民的预期寿命也在逐年增加,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国内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4.83岁,10年间增加了3.43岁。伴随人口预期寿命的增长,大家对自己将来的生活也有了愈加长远的计划。为了可以在退休之后可以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居民也会自觉增加储蓄,从而降低当期消费。 结论与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