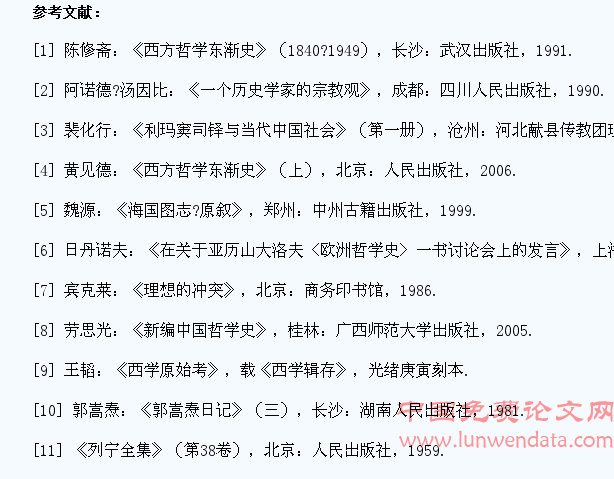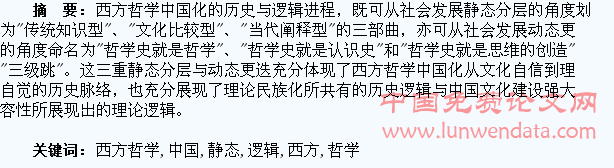
作者介绍:韩秋红,女,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西方哲学中国化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经历与经验教训”,项目编号:12&ZD121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4-0030-08
陈修斋教授曾指出:“既然今天仍旧甚至愈加需要引进西方哲学,那样对于以往三百年或者至少一个半世纪以来引进西方哲学的经历进行一番回顾,总结其经验教训,探索其规律性,以做目前和以后引进工作的借鉴,就是非常有必要,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这工作本来早就应该做了,可惜的是以往虽也有人在这方面尝试过,做过一些初步的或局部的工作,但在此以前还一直无人来对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的过程,做过全方位系统的考察,因而留下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一块亟待填补的空白。”[1](P2-3)现在回过头对这段历史进行总结和深思,发现中国人研究西方哲学的主动意识越创造确,引进、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的目的也越创造晰,达成了从开始时仅将西方哲学作为一种异质文化知道、学习,将它看作是西方哲学与中国文化的外在嫁接,到后来主动在传播、研究西方哲学的过程中打上中国人特有些思维特点、文化烙印,而将西方哲学转基因入中国当地文化,不断生成“中国的西方哲学”。这一转变从社会进步的静态分层来看,经过了“传统常识型”、“文化比较型”和“当代阐释型”三部曲;从社会进步的动态更迭来看,经过了将西方哲学看作“哲学史就是哲学”、“哲学史就是认识史”和“哲学史就是思维的创造史”的三跃迁。经过时空辩证法的一同用途,达成了从“西方哲学在中国”向“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自觉。
1、改革开放前西方哲学中国化的静态呈现:传统常识型
西方哲学中国化呈现为一种“传统常识型”的传播和研究特点。“传统常识型”的特征在于将西方哲学看作类似自然科学普通的常识,对其进行常识化、模块化、结构化的认识。常识的特征是“是其所是”,内涵明晰、简单明了,讲求确定性、规范性,便于学习,所以对常识型科学的认识和传播只可以根据其本来所有些面貌力求原封不动地移植和描画,争取做到“形神兼具”、“形象逼真”。传统常识型的西方哲学研究本质上是将它看作一种异质文化,讲求“还原性”。以达成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空间移植。
如早期传教士传播和推广的西方哲学,自然是根据西方哲学的本来面目引入,期望通过对“原汁原味”的西方哲学的引介和传播,弘扬西方文化精神,达成文化入侵。“他们不仅为了探寻财宝和权力,而且一心要传扬征服者先辈的西方基督教。他们传扬基督教的热情是狂热的。”[2](P173)比如,利玛窦就过去说过:“大家耶稣会同人,根据本会成立的宗旨,梯山航海……做耶稣的勇兵,替他上阵作战,来征讨这崇拜偶像的中国。”[3](P1-2)这样来看,“传教士来华传教的根本目的,在于使中国皈依基督教,进而使中国成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4](P34)。自洋务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的西方哲学东渐,虽然某种程度上已开始与中国人救亡图存的客观实质相迎合,但也正由于中国人有转变落后挨打局面的主观愿望,在向西方学习方面,也愈加努力去描摹西方文化的“真精神”,力求以西方先进文化拯救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师夷长技以制夷”。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就过去表达过如此的看法:“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厉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厉害相百焉。”[5](P67)从而中国人本着知道西方、学习西方的目的,从西方引进技术、引进规范、到引介与传播西方哲学及西方文化,至少在扩充常识的层面上,使中国人愈加知道世界;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间,国内的西方哲学研究呈现出向苏联学习的一边倒状况,苏联哲学几乎成为国内西方哲学研究的“圣经”,甚至将西方哲学等同为苏联式的哲学,几无删改的“拿来主义”,将“还原西哲”推向极致。如1950年李立三翻译的《苏联哲学问题》一书中就引述日丹诺夫讲话中对西方哲学的批判:“把那些原来是黑暗权势和僧侣们所穿着打扮的破盔烂甲:梵蒂冈和人种论,搬了出来,――都搬出来当做武器。”[6](P29-30)也批判了现代西方哲学,觉得“现代资产阶级已变成了反动阶级,因而它的哲学也和哲学理论以往进步的收获断绝了关系。这就决定了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基本内容和社会使命乃是为资本主义关系充当辩护者”[6](P14)。这种局面直到“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拓展才得以转变。可以说,西方哲学东渐是一部对西方哲学常识进行引介与推广的历史,是根据西方哲学的“本来面目”试图不断“还原”和“回归”的历史。当然,任何外来的东西刚开始在他国、他地的进步大概这样,当属正常。只是大家是在比较的意义上对之加以总结与概括。
西方哲学中国化表征为一种常识性的特点和还原性的倾向,大致基于以下两个缘由:第一,任何一种异质学问的引入,开始之初都要体现为一种常识性的引进。“用哲学语言表述,要认识一个事物,就是要把这个事物对象化,然后才大概正确地认识它。”[4](P5)美国学者宾克莱在 《理想的冲突》一书中也提出:“一个人在对他可以委身的价值进行探索时,要遇见很多竞相争取他信从的理想,他若要使这种探索得到满足,就需要对各种理想知道一些。”[7](P1)即在引进常识初期,势必体现为对常识确定性、规范性的尊重。西方哲学的引进、传播和进步亦是这样,只有先对西方哲学史上的代表人物、代表看法、学派分类、思想特征都进行常识化、模块化的介绍和梳理,才能对整部哲学史有一个相对明确的总体认识,并最后串联出一部逻辑严密、一以贯之的哲学史,由于“一部哲学史,虽然是史,但也需要是哲学”[8](P1)。西方哲学进入中国早期,便第一体现为一些要点方面的介绍,人物史、学派史、断代史等成为日后进一步研究的基本素材和较为坚实的基础;第二,大家以一种知性思维和“如其所是”的态度对待西方哲学,还由于自洋务运动后西方哲学进入中国始,刚开始引进和接触的就是西方近代培根的思想。中国学者王韬先后写作《西学原始考》、《英人培根》等著作介绍培根。培根批判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哲学一直惯用的逻辑推理法,觉得科学研究应该从经验事实出发再抽象概括出原理,即提出了总结法,对科学研究的办法进行革命。王韬觉得,正是培根的新科学办法推进了西方科学的进步和文明的进步,为“后二百五年之洪范”,因此大家进行科学研究也应该“实事求是,必考物以合理,不造理以合物”[9](P31)。这种“务在实事求是”的态度也被中国学者继承,用以改造中国以往的文风和学风。近代中国思想界的先驱郭嵩焘在去英国家公务员考试察后,于1877年的《日记》中就写道:“英国讲求实学自毕尔庚(作者注:培根)始。”[10](P268)接着指出培根开启了西方格物致知的新办法,因而西方社会在认识自然规律、推进科学进步方面进展迅猛。有感于此,他沉痛谴责:“中国章句之儒,相习为虚骄无实之言,醉梦狂呼,顽然自至……中国之所以不可以自振,岂不由是哉!”[10](P789)其实,中国语言讲求微言大义、意在言外,重体悟和觉解;而西方哲学重定义,讲逻辑,分条缕析,层层推进,易将事物的内涵和道理讲了解,但也容易因为缺少诗意而陷于抽象定义的王国。中西哲学思维方法、话语方法的不同不从优劣讨论可按相互借鉴对待。所以期望通过刚刚接触到的西方哲学来学习西方人定义式、规范化和看重逻辑推演的研究方法成为可能。这种尊重常识、看重科学的治学精神也被用于西方哲学的引进和研究本身,试图以一种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办法对待西方哲学,旨在对哲学“材料”先充分占有再“总结”,对其进行“白描”式的刻画,“务在实事求是”地“还原”西方哲学的本来面目。 2、改革开放后西方哲学中国化的静态分层:“文化比较型”和“当代阐释型”
伴随改革开放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拓展,国内学术界对学术研究所应秉持的态度和办法不断进行深思,从以往那种仅仅将西方哲学看作是“固化”状况的常识,转变为将西方哲学看作是一部活生生的、灵动变化的西方人思维能力进步的变迁史。如此,西方哲学史便不再只不过一些生硬呆板的“人物”、“学派”、“原理”、“定义”、“命题”的集合体,而是表征着每个时期西方人对世界独到的理解方法和阐释方法。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所表达的看法:“哲学史,因此:简单的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11](P399)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展示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历史。因此,西方哲学史是最可以体现西方人个性化的思维特征、不同历史时期阶段化的文化品格和将来社会差异化的价值诉求的知识。如此,西方哲学史就由以往的“常识史”、“科学史”转变为“认识史”、“文化史”。大家研究西方哲学就是进一步达成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收获”[12](P533),以一种愈加科学和包容的态度吸纳所有出色文化。甚至于正是由于有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对世界不一样的认识和阐释方法,即不一样的哲学样式,所以才会衍生出各年代、各区域、各民族不一样的文化样式。所以,大家将如此的哲学研究称为“文化比较型”,在此意义上,20世纪后20年的西方哲学研究才如雨后春笋般如火如荼。几代学者汇聚成一支重新引进、传播、发扬和深思西方哲学的生力军;中华外国哲学史掌握和全国现代外国哲学掌握等专业研究会纷纷召开;《哲学研究》、《哲学译丛》等刊物纷纷恢复或创刊;“西方哲学讨论会”等各种全国性或地方性的西方哲学讨论会纷纷举行;理论研究中出现了“萨特热”、“弗洛伊德热”、“尼采热”等热潮;另外,现象学、后现代主义、剖析哲学和美国哲学等学派的研究也推向纵深。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后20年的西方哲学研究成就,无论是专著还是译著,论文还是译文,都远远超越了前面整个时期的总量。而且,此时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哲学,已不再满足于单纯传播西方哲学的历史史料和对西方哲学史进行简单的线性勾画,而是在已占有相对较为丰富的史料的基础上,愈加关注研究西方哲学史上思想家之间看法的比照,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比照,在古今对话和中西对话中互为参照系而加深彼此的认识。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西方哲学研究呈现为“文化比较型”的研究范式。
“文化比较型”的西方哲学研究得以拓展与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变化密切有关。从国际环境看,新时期世界范围内常见出现了跨文化研究的热潮,亨廷顿、斯宾格勒等人的思想被纷纷引介和翻译成多国语言,为人类认识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视角和讲解原则,不同文化甚至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也渐渐获得认同;从国内环境来看,随着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大家对世界范围内现代化的进步路径和现代文明的不同走向及其缘由的探究越发产生兴趣,在文化比照中进一步考虑中国社会将来的进步方向和中国文化的合理建构模式。因此,“文化比较型”的哲学研究范式从以往单方面“直观”西方哲学转变为在不同坐标体系中重新认识和讲解西方哲学。假如说“传统常识型”的西方哲学研究是从“正”面探究西方哲学“是什么”,那样“文化比较型”的西方哲学研究则是从它的“反”面,即中西哲学比较与对话中探究它“不是什么”;假如说西方哲学东渐时期,中国学者还渴求以一种“考古学”式的科学主义精神力求对西方哲学进行“复原”,追逐“原汁原味”的西方哲学,在哲学研究中愈加强调查究客体的客观性,那样此时国内学者已开始有了研究过程中的主体意识,讲求的是主体与客体的对话,既包含古今对话――挖掘哲学史上各种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也包含中西对话――在对话中说明各自的理论特质,还包含文本与读者对话――以研究者的思想解析文本的思想,达成思想间的互动与通达。由汪子嵩主持,范明生、陈村富和姚介厚参加撰写的多卷本《希腊哲学史》就是这一转变的开启性代表。作者一方面对原著进行逐句、逐篇的考据,挖掘各篇著作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且对希腊哲学史进行断代史意义上的精雕细刻和通史意义上的古今互释,既有一定性评价,又有否定性批判。同时,作者还主动吸纳古今中外研究希腊哲学的成就于一身,从宏观上推进了古时候希腊哲学的认识与研究,“使西方学者感到以不通中文为恨”[4](P1006)。赵敦华在执笔由朱德生主编的《西方哲学通史》第一卷时,也深感哲学研究要从以往那种“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研究中解脱出来,要既踏实地叙述史实,又对其进行客观评述。因此有学者评论它“资料翔实,视线广阔,持论公允,融学院式理论探讨性与教程的理论规范性于一体,超越了西方哲学史两种通行的写作范式,标志着国内西方哲学通史写作在学术水准和办法论上的要紧突破”[13]。另外,王淼洋与范明生写作的《东西哲学比较研究》、谢龙写作的《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新论》等专门研究中西哲学比较的著作也都在这一时期问世。这类著作不再只局限于西方哲学本身,而是开始关注中西哲学的比较,在研究中渗透着研究者的独立考虑和评判,彰显着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味道,并进一步影响着新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的西方哲学中国化呈现出一轮新的进步态势。“中西哲学交流的历史告诉大家,今天哪个也不能离开哪个,唯一的出路只能是以中国人的语言讲述世界的故事。”[14](P545)这就需要大家以一种人类性的视线和世界性的见地重新看待西方哲学,在“大哲学”观的意义上推进哲学的新进步。所以,中国人渐渐生发出一种以中国人的文化血脉、思维方法和话语方法来阐释西方哲学的新认识。所谓“阐释”,就不同于以往的“还原”和“复制”,而是愈加强调查究者的主体性,根据研究者的目的需要重新“创造”更具年代感和更符合中国人需要的新哲学。也就是说,以“中国人的见地”看待和研究西方哲学,“这里说的中国人眼光,有特殊的意思,指的是一种文化意识和理论标准,它决定着大家察看问题的角度、讲解模式和表达方法,与选择素材和审视结论的价值取向”。[15](P13)近十几年的西方哲学研究,愈加强调在中西哲学对话基础上的融通,在引介、深思基础上的“重构”,在交流互动基础上的“再造”,大家将如此的西方哲学研究方法称为“当代阐释型”。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哲学研究的重地纷纷推出一系列可以体现其独特考虑的西方哲学史多卷本著作,很多国内哲学研究的泰斗也都形成共识,推出一系列可以代表其看法的论文或著作,彰显了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新水准和新气象。 “当代阐释型”的西方哲学研究方法,在对西方哲学已占有相当容量的常识储备和对其哲学特质有相对明晰认识的基础上,中国人开始对已进入中国的西方哲学的地位、功能、性质进行再理解和再阐释,愈加带上中国人独特的理解方法、解释方法,使“西方哲学在中国”为“西方哲学中国化”。用中国眼光和现实问题研究西方哲学,使西方哲学成为中国学界进行中国理论和问题研究必不可少的“生活世界”。正如大家今天学习西方哲学,一方面将它注入当代中国哲学的思想理论之中,构筑富有兼容并包、宽容大方的哲学品格的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其次是为了通过对西方哲学的再认识、再解释和再创造,在世界范围内彰显当代中国哲学的理论水平与当代中国哲学进步的新气象。所以,新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研究,即“求异”也“求同”,追求中西哲学在对话基础上的融通与西方哲学在中国大地上的新成长和再创造。中国学者对待西方哲学也不再只不过“如其所是”的“白描”,而是依据中国人的理解方法和进步需要进行全新的“写意”,推进西方哲学真的达成“中国化”。
恩格斯说过:“在社会历史范围内进行活动的,是具备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什么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自觉的意图,没预期的目的的。”[16](247)新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中国化之所以会体现为“当代阐释型”的理论形态,一是西方哲学进入中国后在时空转化过程中,已渐渐融入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达成着自己的“基因改良”。二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行进,中国人愈加以一种开放的胸怀兼收并蓄,中国文化理论界可以延续和进步出具备独立意识、独立品格的自己文化,向世界宣传中国的文化世界和价值观。为此,国内的西方哲学研究越发看重对西方哲学在新形势下的再创造和再进步,从“西方哲学东渐”转变为“西方哲学中国化”,从“还原西哲”到“中西哲学融通”,创造与新时期进步相匹配的,融涵中西哲学智慧的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
3、从“哲学史就是哲学”、“哲学史就是认识史”向“哲学史就是思维的创造史”的动态更迭
从西方哲学进入中国大地开始,西方哲学作为一种新常识和新文化便不断地经受着中国人的辨识、同意、认可、融通,中国人以何种致思方向进行研究,便决定了西方哲学以何种面貌展示。而中国人在考虑和解答这个问题时,恰好历程“哲学史就是哲学”、“哲学史就是人类认识史”、“哲学史就是思维的创造史”的“三跃迁”。
西方哲学在中国刚开始体现为“传统常识型”特点时,是具备历史合理性的。探其根源,大概黑格尔“哲学史就是哲学”的论断影响了当时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的研究。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曾提出:“哲学是理性的常识,它的进步史本身应当是适当的,哲学史本身就应当是哲学的。”[17](P13)意指哲学史“不可能是偶然事实堆砌的历史,而是那个唯一真理借用这类事实不断自我显现的历史,也是哲学自我进步的历史”[18]。这里的“唯一真理”是指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绝对精神,所以“哲学”是关于绝对精神的知识,而“哲学史”就是展示绝对精神自我运动、自我发展趋势的历史,因此“哲学史就是哲学”。黄见德在《西方哲学东渐史》中进一步讲解这句话:“哲学史是一种独特的历史,它不同于其他的科学史,譬如生物学史,它本身并非生物学。哲学史不同,它不只展示哲学内容进步的外在的偶然事实,还要昭示哲学进步的内在逻辑和哲学内容本身。因此,哲学史本身就是哲学。”[4](P1237)在“哲学史就是哲学”的意义上理解西方哲学,就是强调“哲学”是“哲学史”内在的依据,它既是哲学史的源头活水,又是哲学史一以贯之亘古演变的逻各斯。所以在西方哲学中国化历史过程中,中国学者觉得要先对西方哲学史上每个时期主要代表人物、代表看法等“哲学”材料进行一种首要条件性占有,学会足够“多”时才能为日后的史学工作做好积淀。
“哲学史就是哲学”的认识方法实质上是一种本体论的思维方法。好似西方哲学史自己在其历史早期出现的本体论阶段一样,从存在论上说,将西方“哲学”的常识和素材看作是“实体”、“本体”普通的“客观存在”,这种实体式的、固化状的客观存在有其自己的存在样式和变化规律,西方哲学史就是对这个规律的展示;从认识论上说,体现为一种对象性的知性思维和符合论的真理观,抛开对研究主体思维能力的剖析而直接对西方哲学史进行认知,追求认识的客观性;从办法论上说,讲求研究者对西方哲学史只能进行“如其所是”的描画,“务在实事求是”,期望“复原”出一个“是其所是”的“西方哲学”。所以在“哲学史就是哲学”的本体论思维方法指导下,不少类似“考古”的西方哲学史研究工作相继展开,“人物”、“典籍”、“文本”等考据、翻译等工作获得了很多进展,在常识性引介方面达到了科学和客观,“确切、简洁、清通可读”[19](P304),易于理解、便于学会。所以,本体论思维方法的最大特征是对象性思维,将哲学视为如科学常识一样的常识,以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哲学,哲学变成了某种“科学常识”的“历史”。因此,西方哲学被引介之时便是国人知道之际。
西方哲学在中国的进步经历之所以会渐渐走上西方哲学中国化的道路,并渐渐呈现为“文化比较型”的特点,与思想范围拓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紧密有关。中国学者可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讲解原则看待西方哲学史,同意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表达的看法:“哲学史,因此:简单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11](P399)以“哲学史就是认识史”为原则研究西方哲学,西方哲学史体现为人类认识有规律的历史进步。认识的背后是主体的觉解和思想的植入。因此在“认识史”的意义上研究西方哲学,一方面要辨析了解每个历史时期“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及其历史变化和规律,其次也要看重从思想性、文化性入手,探究哲学思想诞生背后的历史首要条件、年代背景、问题导向、理论蕴含和价值关怀,在历史的开荡中挖掘西方哲学史所表征的人类理性思维发育的历史和在社会的延展中捕捉西方哲学所深蕴的西方社会的年代问题和文化内涵。既然“哲学史就是认识史”的研究原则是对主体思想的一定,那样这一时期的西方哲学史研究也在一定量上开始一定研究者对哲学史的解析。如此,西方哲学在中国人眼中就从“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常识史”转变为“哲学史就是认识史”的“文化史”。 这种转变好似西方哲学自己由古时候本体论阶段向近代认识论阶段转变一样,假如说“‘认识论转向’是从古时候哲学离开对人类认识活动的检讨而追求世界统一性的本体论独断,转向对‘人的认识何以可能’的认识论深思”[20](P1),那样国内西方哲学研究的这次转换就是从以往抛开对人类思维能力进步水平的考察而单纯追求西方哲学常识的客观性,转向对人类思想和文化的进步史的觉醒。这是对西方哲学研究自己的“反躬自省”。“哲学史就是认识史”愈加看重哲学家所面临的具体的历史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性价值,挖掘哲学史作为思想性的历史的内在逻辑机理,强调不同历史时期思想看法之间的前簇后拥、更新换代、常驻常新,与中西方哲学差异所表征的文化差异。这种思想的觉解意味着不受首要条件性认识的束缚,可以以思想的深思性和批判性为首要条件,重新看待历史、建构体系,重视在西方哲学研究中注入研究者自己的考虑和主体认识自己的二次建构。假如说以往“哲学史就是哲学”的思维方法单纯追求常识的客观性和确实性,那样“哲学史就是认识史”的思维方法则强调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强调查究者的思想对哲学史的改造;假如说以往“哲学史就是哲学”的思维方法侧重追求西方哲学的“如其所是”,那样“哲学史就是认识史”的思维方法则侧重追求西方哲学的“如其所不是”,从西方哲学展陈出来的常识结构中挖掘其背后深层次的思想逻辑及与中国哲学相比照而呈现的不一样的文化内涵;假如说“哲学史就是哲学”的思维方法侧重科学主义的一定性思维,那样“哲学史就是认识史”的思维方法则愈加挨近哲学的否定性思维,以哲学思想的批判深思为否定的辩证法,将西方哲学看作哲学思想否定进步的历史过程,也将西方哲学研究看作是“思想”否定“存在”的过程,将西方哲学看作是一部否定之否定的具备内在超越性的文化史。当然,“哲学史就是认识史”的思维方法也存在肯定的问题。譬如,无论大家怎么样进行中西哲学的比较和对话,其实质都还是将西方哲学看作是一种异质文化。
21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中国化经历表现为“当代阐释型”的特点,是理论界进一步追问到底该怎么样看待和研究西方哲学而做出的新调整。在此看法下的西方哲学研究,就是为了融西方哲学于自己的哲学进步之中,体现本民族理性思维的创造性活动,表达源于己关于哲学的独到理解和全新阐释,体现中国人我们的自由追求。也就是在“照着讲”、“接着讲”的基础上,还要“自己讲”[21],讲出具备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当代中国新哲学。在这个意义上,大家将21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中国化经历称为“当代阐释型”,表征着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自觉。
“自己讲”与西方哲学在现当代出现的语言学转向密切有关。在本体论方面,摒弃以往将西方哲学史看作是常识大全或认识进步史的窠臼,而将西方哲学与人的存活处境相联系,觉得哲学以其特有些“定义”、“思想”为载体,阐释着对人类“精神故乡”和“安身立命之本”的终极关怀;在认识论方面,从以往的对象性认识转变为生成性认识,强调主客体的互动,主客体的互动过程就是创造思想的过程;在办法论方面,看重语言剖析和意义阐释。哲学作为“创造性的知识”、“自由的思想”,也体目前它的语言上。正像德勒兹对“定义”的看重一样,哲学创造一组特有“定义”,并对其进行独到阐释,就是开创一种对世界的理解视角,也就为人类的存活提供一种全新的向度。不一样的哲学家以不一样的“定义”表征不一样的思想,同一“定义”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家的阐释也会指代不同内容。这就是对哲学思想的不同理解,才有“接着讲”和“自己讲”的可能性和价值性。“正如人之存在的历史性一样,哲学作为人的本质的存在方法,势必表现为哲学史。因此,哲学史并非大家一般理解的给定的僵死的历史,而是充满活力的不断成长的历史。”[22]黑格尔对语言的看重并身体力行地用本国语言努力阐释本民族的思想,海德格尔的“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与波普的“三个世界”理论等,都表明语言是思维的载体,语言的创造就是思维的创造,思维的创造就是人类能力的进步。因此,在“哲学史就是思维的创造史”的理解中,国内的西方哲学中国化愈加强调哲学创作者与哲学解析者的互动,强调哲学研究过程中思想和意义的创生,对意义性的阐释和再造变得愈加自觉,“在常识、思想和意义的三位一体中重塑西方哲学”、“让西方哲学讲汉语”(邓晓芒语)成为一种新的召唤。由于,“哲学史就是思维的创造史”不止是对哲学本身的进步,更是对人类存活空间性的扩增,体现了哲学“向上兼容”的本性和无限发展的生命力。所以,以西方哲学中国化为致思方向,以中国人的文化背景、思维方法为理解西方哲学的思想首要条件,以中西哲学融通和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为重新阐释西方哲学的价值旨趣,赋予西方哲学全新的成长点,是大家对西方哲学再创造的将来的道路,是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进步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