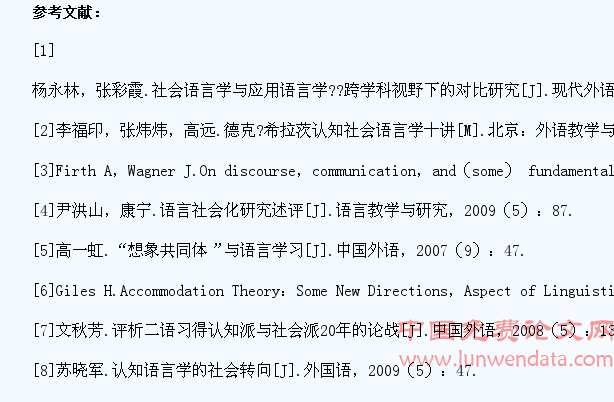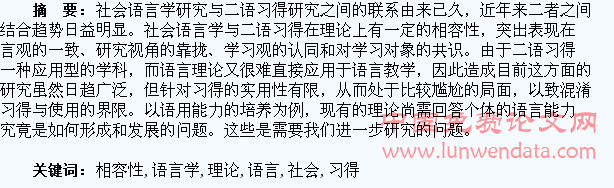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1.021
从社会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的进步历史来看,两门学科都带有多学科性质,经过几十年的进步,其研究范围都先后涉及到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认知科学等范围,二者相互交叉、相互联系。
1984年,英国社会语言学家Trudgill明确提出“应用社会语言学”这一定义,进一步推进了社会语言学在应用方面的研究。美国社会语言学家Hymes于1972年初次提出的“交际能力”定义,在二语习得范围直接引发了教学变革,由此进步而来的交际教学法盛极一时,成为现在社会语言学与二语习得结合得最好的例子之一。进入1990年代,伴随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日益兴盛,与在实用研究方面把研究范围扩展到外语习得环境中文化及社会原因所产生的影响,社会语言学已与二语习得的研究范围重叠[1]。同时,因为二语习得范围社会文化理论的影响和社会文化派的崛起,社会语言学研究同二语习得研究的结合趋势愈加明显。
现在学界对社会语言学与二语习得相结合的研究虽呈上升趋势,但从发表的有关论文来看,多数研究提出外语教学中应重视交际能力、语篇教学、社会文化原因,而对教法改革背后的理论阐释却倾向于简单化处置,语言习得理论看上去薄弱。本文拟从语言观的一致、研究视角的靠拢、学习观的认可、对学习对象的共识四个方面对二语习得和社会语言学进行理论的梳理、比较与阐释,力图厘清有关定义,发现二语习得的社会学路径及与社会语言学在理论基础上的相容性,从而达到发挥多学科交叉的优势、丰富二语习得研究视角的目的,同时深化社会语言学应用研究范围,增加语言教学方面的实用性,增强社会语言学理论的阐释力。
1、语言观的一致:语言是社会现象
语言符号本身具备社会属性。语言产生于肯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其存在本身是为了服务于社会成员间的交流。谈话可以打造社会关系,对话中的语言起着传递说话人信息有哪些用途。多语社会中不一样的语言有不一样的功能,双言现象、语言变异理论、标准语和方言的关系等理论研究,都有力地揭示了社会中语言形式及其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对语言具备社会属性的一定。
从语言学理论的进步历史和社会语言学的兴起来看,语言学的进步历程了一个从承认到否定,再到不再质疑语言符号的社会性的过程。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一定语言的社会功能,用语言/言语把语言作为社会性系统与个体的实质用区别开来,但缺少对个体系统的讲解。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将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作了区别,但因此而扔掉了语言的社会性,使语言脱离了各种语境成为同质性理想化的存在。事实上,语言同语义、用、社会、文化等原因密切有关、很难分割。在质疑乔姆斯基理论的基础上,语用学、社会语言学等关注语言与现实世界关系的理论渐渐进步起来,并纷纷形成各自独立的语言学分支。[2](P1-17)把语言当作社会现象来研究由来已久,研究语言符号的社会性是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缘起。研究语言需要联系社会实质,这是社会语言学的基本出发点。
在二语习得范围,1970年代以来,心理语言学理论占有要紧地位。主流研究把语言当作心理现象,关注学习者的个人心理特质,而忽视了语言产生和用的社会环境有哪些用途。
1990年代以来,推崇Vygotsky社会认知进步理论的学者则强烈反对把语言和语言习得与社会环境相离别,开始探索该理论在二语习得进步过程和教育中的应用,由此开创了从社会文化视角探索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作为一种研究高级心理机能进步的理论,Vygotsky社会认知进步理论强调社会活动在心理进步中有哪些用途。语言是联结个体与外面之间关系的主要工具,在高级认知中起着中介用途。语言具备双重属性,对外是社会互动的单位,对内是思维的单位,通过对话活动来协调社会活动和高层次的心理进步。语言作为符号工具用包括着间接经验,与带有独特社会特点和文化信息的社会情境紧密相连、没办法分割,言语能力的形成是在社会支持系统下通过认知过程达成的。语言学习就是社会活动与认知过程联系在一块的社会文化现象[3]。
语言社会化在二语习得的社会化路径中占据要紧一席。语言社会化理论和社会文化理论虽均遭到Vygotsky心理学的影响,在研究目的上却不尽一致。社会文化理论关注的是认知能力及语言能力的进步,而语言社会化理论则关注的是文化常识与语言用能力的一同进步。语言社会化理论最早由人类学研究者Schieffelin和Ochs提出,他们将它概念为儿童或新手通过语言形式的学习达成其社会化的过程,其间包含同意相应的价值观、行为方法和社会风俗。这方面的研究表明,语言与社会环境之间相互依存、很难分割,语言习得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其与社会文化相适应的过程,即个体的社会化过程。[4]特定的语言和其存活的社会文化环境是一个整体,每个组成部分相互依靠、相互用途。
在社会语言学范围,围绕结合社会原因探索语言问题这一观念,Firth继承和发扬了Malinowski关于语言是一种行为方法、具备社会功能的看法,强调要把语言放到整个社会环境中去研究,提出了言语情景的定义,创立了语言学研究中的语境学说,觉得语言的意义就是其在语境中的可能。随后陆续发表的语境和语域理论范围的研究成就充分说明,在人用语言认知和交流的过程中,一定会程度不一地遭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当然环境中也包括历史文化风俗等原因。正由于这样,社会文化理论觉得,人的高级层次的认知取决于社会文化原因。最新的二语习得研究成就已经证明,语境的每个方面都影响着语言学习的过程。如Norton从身份构建这所有入点出发,揭示了社会文化语境形成的二语习得者与目的语之间的势力关系,与这种关系对二语习得过程的影响。[5] 正由于语言具备社会性,所以语言习得(即语言常识的构建)非常难与语言产生和用的社会文化割裂开来。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来看,二语习得的社会学转向一定了语言的社会性,认可语言是社会现象而非心理现象,语言常识和能力的构建与学习者的环境体验和社会交际密切有关。从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派的角度来看,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就充分一定了语言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将二语学习的社会原因理论化,并且通过这个宽泛的框架,为二语研究注入了社会化理论。
2、研究视角的靠拢:对交际互动的看重
二语习得研究范围目前较为活跃的社会文化派与认知派理论上的最大分歧在于,社会文化派不同意学习发生在个体内部,而觉得人的高级认知源自社会交往活动,因此特别强调交际和互动在认知及语言进步过程中有哪些用途。因为交际本身是通过语言来达成的,如此,身心、内外或思维和交际活动就通过语言符号得到了统一,即交际活动中的语言运用在心智功能进步中起着核心用途。但交流不只只不过语言学习的工具,根据Hymes的怎么看,交际本身也是一种能力。语言交际能力问题涉及很多方面,除去语言结构、语境文体、跨文化言语行为意识等方面外,还有文化心理方面的原因。
1960年代,受人权运动年代的影响,语言问题成了突出的社会问题。基于Fishman对移民语言情况的考察,Bernstein对不同阶层成员,尤其是儿童语言的考察,与Labov对黑人英语的调查,社会语言学在兴起之初已发现三条要紧的原理:语言与社会是相互用途的;大家大概学会几种结构各异的语言或变体;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语言规划和社会规划加以改变。也就是说,在社会语言学研究者看来,社会中的语言用户拥有用变体的能力,对变体存有主观态度,可以在交际中加以选择用。
语言系统是异质性的,充满内部变异。语言作为社会现象,与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系统联系在一块,从心理学角度考察语言用户对语言变体的主观认识和态度,与上述带有社会性质的评判对语言用户言语行为的影响,是社会语言学主流之一语言社会心理学的中心课题。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因此从个人角度研究说话人对语言的态度是可行且必要的。语言态度归根结蒂反映了对语言用户和使用方法的态度。对社会心理的考察,主如果通过心理实验的办法获得研究素材,如配对变语法测试受试者对操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态度,并且常常结合用语义微分尺度,使说话人的特征得到更确切的剖析。语言社会心理学对语言态度的研究,大大加深了大家对语言与社会的关系、语言在社会交流中有哪些用途的理解。这方面的研究成就对二语习得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Lambert和Gardner的二语习得中的态度与动机理论,其研究重心主要放在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态度、动机对他们最后的成功所具备的影响之上。研究结果表明,二语学习者对所学语言的态度会干扰其习得成效。
Giles的言语适应理论是继Lambert办法后该范围在理论上的新进展,也是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语境中交际者的心态和言语选择行为。语言用户趋同或趋异的言语选择,突出强调了社会交流中语言用户对他们的认可或不认可的态度和行为,讲解了言语交际中风格变化的方案背后的主观情感和动机。[6]言语适应理论为语言变体研究增添了动态的角度,体现了社会语言学自己从典型描写到讲解预测的研究进步路径。这种讲解性的努力在一定量上弥补了Labov对语言变异描绘精细但局限于静态的不足。另外,这方面的研究也凸现了个人是怎么样通过语言选择来显示我们的社会文化价值的。在社会建构主义影响下,社会语言学觉得,语言与社会原因可以被视为是相互建构的:身份影响语言的用法;语言的用法也是塑造身份的过程。
总的来讲,社会语言学的进步与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派重视真实语境、身份和体验,这与多种语言互动的倡导不谋而合。从理论上讲,目前社会语言学理论框架中语言变异研究的成就,如语言变体的辨识、语域的认知等,为交际能力的培养和评价提供了系统的、受社会条件影响的二语变体数据,对二语学习具备指导意义。语码混合、语码转换及言语适应方案等交流中的言语选择,使交际语言运用能力目的得以形象化地表达。对交际中的语言行为,如道歉、赞美、邀请、拒绝、请求等的研究,为二语习得跨文化言语行为意识的培养勾画了进步目的。
3、学习观的认可:基于用的学习
如前所述,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派倡导学习是一个内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始于人际交往的。对于二语学习者而言,非常重要的是与人交往,在交往互动中进行意义的建构。譬如,学习者比较容易注意到词语的习得随着着对肯定社会文化情境的深入知道,在不一样的语境中,词语意义或许会发生改变,语言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并不固定。对范畴的学会意味着依据交流需要对语言规范遵从或背离。事实上,语言的习得和用并没一个明确的界限,语言是人际交流、社会活动的中介,而言语交流一直发生在肯定的社会语境中,因此语言学习即语言用。反过来,语境中对于语言用也可以巩固和加大语言学习。这样来看,社会文化派的语言习得理论觉得习得过程即语言的用法过程,觉得真实世界中用的语言对学习来讲是根本性的而不是辅助兴的,用不是习得的结果,更不是方法。正由于社会文化派坚持在语言习得和语言用间划等号,这样强硬的立场招致了认知派倡导二语习得研究的对象是二语习得而不是语言的用法的激烈批评,反对把二语习得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二语在真实语境中的运用[7]。
在习得即便用这一点上,社会文化派完全可以从社会语言学范围中的最新流派――认知社会语言学那里找到强有力的理论支撑。认知社会语言学是认知语言学的体验哲学观和经典社会语言学理论相结合的产物。认知语言学关注语言的常见原则与人的认知之间的关系,但因为语言意义并不是孤立存在,是在人类互动中产生及传递的,因此认知语言学所理解的语言定义及其基本结构也关系到社会和文化情境下的认知。伴随认知语言学的不断进步,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从话语和功能的角度研究语言,愈加关注语言的社会性。基于使用方法的倡导本来就是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立场,认知语言学觉得语言常识源自用,说话者为了交际和社会交互的目的识解自己体验,而听话者也为同样的目的识解释说明话者的话语,因此认知语言学渴望对语言的社会交互性做源于己的贡献[8]。上述缘由将认知语言学引向社会变体研究。对于在基于使用方法的办法论体系中该怎么样理解语言系统、为何变体研究具备重要程度的问题,认知社会语言学家Geeraerts觉得,因为语言用的行为是语言学的最基本事实,语言系统只被看作是对语言行为中出现的模式进行抽象和概括。他谈到,“There is usage,there i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eople,the interaction is socially structured,and the linguistic system is an abstraction over that social structure……”[2](P34)。可见,语言用户学习语言的过程并非将自己与所谓的系统进行校正的过程,而是在社会互动中与其他语言用户相互调整的过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Geeraerts觉得,因为每一个人的接触范围有限,这类调整都是不完全的,并具备各自的社会结构。因此,在基于使用方法的办法论里,语言变体研究是语言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要紧组成部分,社会互动影响了语言用户的个体语言常识系统。 综上,结合语言习得,可以有如下理解。第一,任何语言的用法者都是学习者;第二,习得不可以简单地被看作是结果,更应将它看作是一个永远的、不间断的过程;第三,应看重真实的语境、不一样的参与者、不一样的身份,应看重不一样的社会语境、交际者、社会群体致使的隐喻变异,看重隐喻背后的文化模式,其重要程度可能不次于教室语境。
4、对学习对象的共识:关于规范和标准
语言的变异性和标准化都是社会语言学的要紧研究内容。面对语言内部变异和动态进步的事实,有必要编撰一整套言语社会遵循的统一规范,来对上述状况有意识地压制,以便服务于国家化进程、国家象征、社会统1、实质需要与学校教育的拓展等。这就是标准语产生的缘由。其本质也是一种发生在肯定社会和历史空间中的语言变异现象。
根据社会语言学的看法,语言变体没优劣之分。从功能的角度看,语言形式对应社会功能,社会语言学关注的是交际功能和交际任务的完成及其效应。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标准语具备较高的社会威望,能满足适应较高语体的功能需要,但不可以由此觉得标准语就比其他变体更为优越。
从学校教育角度上来讲,课堂教学也需要一套规范,因而标准语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学校教育的强化,学习者倾向于觉得标准语形式是正确的,而其他方言和变体形式是不对的、不规范的、听起来是错误的。事实上,在交际者感情不认可的场所,如团结模式中,由下而上的力量大概出现对标准语的趋异和背离,譬如,标准语显然很难适应较为低端的语体。另外,标准语虽然守旧,其变化虽然缓慢,但它仍然是有变化的。标准语在语言的每个层面上的规范化程度是不同的,其程度最高的是书面形式,较低的可能是它的语音。尤其是在当今语言国际化、多样化、多文化、多变体的形势下,从语言用的角度来看,二语学习者应尽可能知道语境和身份的多样性,尽量地增长变体的常识和用变体的体验,以有益于二语学习。
5、结语
社会语言学和二语习得虽都研究语言,但各自的学科侧重点有所不同。二语习得研究的重点是怎么样帮助学习者习得语言。对于看重认知及思维、考察个体的认知原因的认知派而言,社会语言学主要流派之一的社会心理学派有关语言态度的研究对二语习得研究是有助益的。二语习得的社会学派看重社会环境原因,呼吁语言学习要看重语言的社会性和互动性;而社会语言学的主要关注点则是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变异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研究语言的功能,研究语言用户在特定语境中怎么样交流互动,正是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强势所在。这样来看,二语习得理论的进步与社会语言学研究对语言和语言学习的怎么看及认识颇有共识,社会语言学有关定义和考虑可以为二语习得研究所用,丰富二语习得研究的视角。
综上所述,理论化的对象几乎都是学习计划,而非学习过程。因为二语习得是一种应用型的学科,而语言理论又非常难直接应用于语言教学,因此导致现在这方面的研究虽然日趋广泛,但针对习得的实用性有限,从而处于比较尴尬的局面,以致混淆了习得与用的界限。以语用能力的培养为例,现有些理论尚需回答个体的语言能力到底是怎么样形成和进步的问题。譬如,如何习得变体的常识,如何学习语码转换,如何学习性别语言等。个体在面对某类个体和其他类个体的时候,如何掌握不同用这类变体?促成这类变体习得的社会力量有什么?这类都是需要大家进一步研究的问题。